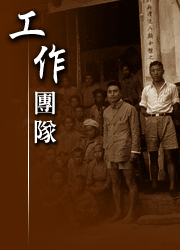| 我的研究主要在於「邊緣」──邊緣的空間、人群與記憶──藉此體現一社會的多元面貌﹐及其間的權力階序關係﹐以及邊緣成為邊緣的歷史與歷史記憶變化過程﹐也藉此了解各種核心主體的文化偏見。我的博士論文即討論由商人到漢代華夏之西方族群邊界變化﹐以及相關的人類經濟生態變遷。在
1992年獲博士學位後﹐我進一步結合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理論﹐並以此應用在族群「邊緣」研究之中。1997
年我出版《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一書。在此書中﹐我提出一個華夏「邊緣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構想。然後以考古資料說明華夏北方生態邊緣的形成﹐以及相關的﹐華夏認同與華夏邊緣的出現。我以歷史記憶與失憶來說明華夏邊緣人群的認同變遷﹐以及因此造成的華夏邊緣之漂移與擴張。最後﹐以台灣與當代羌族為例﹐說明此華夏邊緣之近代變遷過程。 1994-2002年間﹐我利用多個寒暑期在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藏族中﹐進行累計約一年的田野調查。根據這些田野材料﹐以及歷史與民族志文獻﹐我在 2003年出版《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聯經出版)。在這本著作中﹐首先我介紹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上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過程涉及中國與吐蕃之政治、文化勢力擴張下﹐許多人群的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變遷的宏觀歷史過程﹐以及親近人群(男性與女性﹐土司與其子民﹐以及鄰里居民間)以文化與族源相互誇耀、歧視與模仿的微觀社會過程。因而我認為﹐「羌族」不只是一個「少數民族」﹐也是一個「華夏邊緣」與「藏族邊緣」。近代中國國族主義下的「民族化過程」﹐便是將邊疆(frontiers)上的蠻夷(羌人)變為邊界(borders)內的少數民族(羌族)的一個華夏西方族群邊緣的近代變遷。以此﹐我對「羌族」及「中華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歷史語言研究所早年的西南民族調查﹐便是長期中國邊緣變遷中之近代建構的一部分。我們將芮逸夫、凌純聲、陶雲逵等前輩學者之工作﹐以及他們當年所蒐集、攝得的資料透過網路公諸於世﹐便是希望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議題之中。其中一個重要議題便是﹐由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考古學與史學﹐如何貢獻於中國國族主義下的主體與邊緣建構。如此我們並非將前輩學人的研究解構成一種「想像與建構」﹐而是期望這些研究能「映照」(reflex)我們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偏見。 |
| 筆者近年來的研究重點 (1997-present)主要是在: 1. 中國雲南景頗及載瓦人觀的研究, 2. 人觀議題在中國西南族群間的比較研究, 3. 商品、階序與國家在德宏景頗區域及族群歷史上的人類學研究。 在人類學理論上筆者主要的討論脈絡集中在對於人與物的關係(人觀與交換)以及儀式表演階序形成間關係(記憶與遺忘)的討論。筆者認為這兩種理論脈絡對於了解這個區域而言是最重要的,而反過來說,這個區域的材料對於既有的理論也是最有挑戰性的。 在未來的研究上,除了將繼續通過團隊的方式做中國西南地區的比較研究外,筆者個人將集中在對於個人認同與人觀中自我的研究,尤其有關於歷史上不同經驗─從前緬甸的殖民經驗,中國的帝國、土司及國族國家經驗,當前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對於個人與人觀中自我發展的影響。所以我目前的田野研究已逐漸從山居的景頗人擴展到都市的景頗人,從較老的人口到較年輕的人口。 網頁連結: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taff/c9-1-26.html |
| 是什麼樣的心情驅使我來作這份工作……?您應該去過民族所吧!應該也知道民族所的大門,就寫著凌純聲館幾個大字。打從第一次走進民族所,凌純聲是誰?為什麼民族所取了一個和他一樣的名字?這個疑問,就這麼一直被我放在心理。每一次走進民族所,可能只是去拜訪某個老師,或只是為了參加研討會拿論文,總忍不住要多看一眼這個名字。我不太好意思問別人,因為從來也沒聽人這麼問過,也沒聽然談起過,只不過這棟建築物,就像隔壁那座和胡適這個名字連在一起的公園一樣,民族所彷彿理所當然的就應該和凌純聲這個名字連在一起。我想,他大概是一個人類學家吧!要不是這份工作,我恐怕到現在還不知道凌純聲與芮逸夫是何許人也。有些時候,發現過去是為了尋找一種認同,發現學科的過去也是如此,終於你知道自己不那麼孤獨,也不那麼特別,然後覺得自己離上帝更遠了。 將來還會做什麼呢?有些時候,這個問題是再清楚不過了。有一大堆的文書,正等著我們開始進行數位化﹔有一大堆為辨識的照片,等著我們一筆一筆的給他一個名字﹔還有放在文物館庫房、展場裡,或是民族所博物館裡,幾千件的文物,還等著我們為他一一拍攝,寫下註記。光是這些工作,恐怕就得做上個好幾年,也許有朝一日,我們也會像明清檔案一樣,有個工作室,名字或許就叫做西南民族田野工作室吧! 今天又見到甲骨文的總裁預測電腦業已經發展到產業的頂點,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會有很多很多的科技新貴要面臨失業的危機,希望他的預言不會是真的。還好,咱們做西南民族研究的,才剛起步,還有一個遠大的目標支撐著,只要一想起這遠大的目標,彷彿就覺得,未來已經在遠方像你招手,將來起碼再怎樣也會有個還算穩定的工作吧! 將來還會做什麼呢?有些時候,這個問題卻是再模糊不過了。不諱言的,每天早上到辦公室,第一件事是要想想今天要做什麼?寫文件、寫會議記錄、報帳、和別的單位溝通、開會、讀文件、讀資料、設計表格、寫說明等等……做不完的雜事,總是難得靜下來,好好的作一些深刻的思考,偶爾看看地圖、照片雲遊在西南田野,讀讀前輩們留下來的筆記、文章,感受西南田野的艱辛,倒成了每天最奢侈的享受了。將來還做什麼呢?我想,總是一如往常的周旋在每日做不完的雜事之間,不斷地製造問題、解決問題。還是問問我,今天做些什麼工作吧! |
| 我的研究焦點是在地景建築與文化的關係,碩士論文的田野地點是雲南境內通往緬甸古道上的僑鄉。地景建築貌似「自然」,而諸多研究者已提醒我們這才是意識型態的最佳載體,同時,空間的易覆蓋性質與圖像-意義連結的鬆散,又使得地景建築所能承載的論述有相當大的操作空間。人營造環境的背後動力,一方面是試圖操縱論述的產生,使論述有一個得以展演的物質空間,但另方面,論述本身,又回過頭來影響環境的營造。論述與物質,兩者間往復循環,使地景本身成為文化的媒介,主動介入文化的生產,而非只是靜態承載意義的容器。 踏入人類學的知識領域,對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田野經驗。西南的田野經驗對我而言,每一步都把自己投向未知的碰撞。未知的不是田野地裡人事的陌生,未知的是自己在那樣處境中的反應與感受。同時,因為經過方法論課程的洗禮,所以不管是在訪問、攝影或者是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總會直覺得反思我與在地人的關係。 後來參與現職,得以接觸許多珍貴的田野照片。當看到前輩們帶著貴重的儀器,拍下當地人站成一排正面一張背面一張的照片,好蒐集「禮失而求諸野」的資料;或懷著民族主義的情懷,把蒐集得到的資料,放在早已設定好的國族框架裡來解讀時,往往讓閱讀筆記的我強烈感受到驅策著他們前進的遠大使命感。 當科學的大纛現在已成為一個「迷信」的靶子,被筆刀文劍給削落在地時,再對比不過七十年前當年的研究者深深相信科學中立的心態,不禁讓人思索學術氛圍對學術研究的影響。這時候,心情就開始矛盾起來了,一方面是羨慕,另方面是警醒。羨慕的是,當初時代的氛圍給了研究者一個遠大的使命感,警醒的是,如果說科學與民族主義是當時影響研究中立的迷思,那身為一個現代的研究者,我們必須小心的迷思又是什麼? |
| 當其他工作團隊的成員介紹著他們學術的關注與理想時,我想我來談談「瑣碎」的業務工作,畢竟,大部分是這些龐雜的「瑣碎」支持這計劃的推展、並成就其預設的目標。 數位典藏的「專業」大名其實掩蓋了兩個最淺顯易懂的業務內容,一是網頁架構的規劃與內容撰寫,另一則為典藏品資料庫的開發與設計,最後再將兩者合而為一、對外公開,成為一個中國西南族群相關議題的入門管道。而我就是負責資料庫的部分。在文、理有如兩個文化般地難以溝通的時代,十多歲即被「歸類」為社會組的我,對寫程式、架系統可說是一竅不通,而我要費心關照的,是設想一個能夠說明與突出該典藏品特質的資料庫,然後再將這些需求告訴資訊所的人,由他們進行技術層面的開發。當資料庫系統已建立並得以運作之時,這不過揭開另一龐大工程的序,緊接著,我們要為每一筆典藏品填寫基本資料及與之相關的知識內容,這部分則倚賴學有專精的研究者撰寫。 上述的業務流程和目標似乎是如此流暢、明確,但對實際執行的我來說,卻常陷溺在龐雜的準備工作裡,而忘記自己在數位典藏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淑莉所說的,每天一早來上班,都要想想今天要做什麼;也許我每天下班之時,也得一再地提醒自己別陷溺於瑣碎而迷失主要方向。 |
| 我研究的主題是壯族的宗教儀式,以女性的儀式專家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碩士論文處理壯族女性儀式專家的養成過程和其儀式表演,分析的焦點是儀式文本,論點是女性儀式專家的表演,展現與規範壯族社會的親屬間的關係。目前研究的興趣在於壯族做為一個邊緣的族群,如何理解中央王朝。中央王朝對於邊緣地區主要是透過文字記載,中國的邊緣族群對自己的「歷史」的記憶則倚賴口傳。研究方向會朝著女性專家如何透過口傳的傳統來理解中央王朝。討論的議題會包括宗教、性別與帝國。 我是以做田野的心情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做田野的心情,指的是透過現有的出版的資料與庫藏的標本,來理解二十世紀初民族學研究的大時代背景,重溯研究的路線,以及想像當時研究的脈絡。前輩蒐集的資料是豐富的,並留給後輩很多參考的資料和研究的空間。 |
| 本人陳玫妏,1998年自輔大宗教系道教組畢業,進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抱持著「放下經典,走入民間」的自我期許,碩士論文選擇前往中國大陸廣西田林縣,針對屬於大陸少數民族識別中的瑤族支系—盤古瑤,進行宗教與人觀課題的研究。碩士論文於2003年由唐山出版社發行,書名為《從命名談廣西田林盤古瑤人的構成與生命的來源》,為清華人類學叢刊第八集。本論文並曾獲88學年度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訪問學員」寫作獎助,以及91年度《王崧興紀念基金》的獎助。 碩士班畢業後,曾分別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民族所擔任兼任與專任助理工作。期間曾在國科會《島嶼與大陸東南亞的名制、稱謂與集體記憶》計畫(由蔣斌、麥留芳教授共同主持)資助下,再赴廣西針對苗瑤與壯侗語族的族群,進行親屬稱謂與命名制度的調查研究。研究成果涉及親屬結構、稱謂邏輯與文化意義的探討。 2005年考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希望未來能充實語言學與歷史人類學方面的理論知識,進行瑤族儀式文本與文化接觸議題的探討,也希望能對文本分析與民族誌寫作有更深入的涉獵,並開展具有啟發性的方向。 |
| 剛來到這裡,每天的工作就是將手中泛黃的老相片掃瞄成電子檔,原來,這就是數位典藏。一開始,只知道這是一群研究學者,在二十世紀的20至40年代間,踏遍了中國西南地區,拍了許多的相片,做了許多的調查報告。當我開始閱讀文獻之後,發現他們戴著各式各樣的「眼鏡」,來觀看這片地區的「人群」,「眼鏡」的材質不同,所看到的「視野」也就不同了。有些眼鏡的材質是「教化」,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要宣揚「以建民國」,並發展邊疆民族教育,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群落後的人」,自明、清以來不斷有人重複做著相同的事情;有些的材質是「國族」,他們帶著科學的方法,希望藉由語言學、體質學、文字學、歷史學等各個面向,證明這裡的人群是我們的兄弟。 這不禁使我思索:若是我,又會帶著什麼樣的眼鏡來看待這些人群呢?心想著,非得要去中國西南地區看一看,也引領我進入了中國西南民族研究的領域之中。我的碩士論文所要討論的議題是:文本與意識,以《木氏宦譜》(明代麗江府木氏土司的家譜)為個案研究,我要探討非漢民族採用漢族式的家譜書寫,這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意識、族群意識為何? 如果,吸引更多人加入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是這個分項計畫的目的之一,那麼我就是那個被吸引的人吧! |
| 認同與物質文化 |
| 人群的認同是具有多層次,並且充滿了不確定性,而物質文化提供了將認同以原本的心靈思惟,將之轉變為人人可加以閱讀、解釋與詮釋的文本,這一類的文本、物質文化,不只是包含了可以藉由肢體感知到的物體,同時也包含了文字、口頭論述、音樂、地表景觀的改變,各種可以經由感知器官察覺到的物質文化。人們如何透過物質文化,表達內心的想法,他們的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對應關係,從思索到實際的製作、創作,會受到技術、材料、概念的影響,使二者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扭曲、變形。人們對於生活中所創造、感知的隱喻,而這些隱喻揭示了人類心靈的的對應原則,所以可以藉由研究其中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檢視轉變的機制。筆者目前的主要研究趨向,是藉由"概念隱喻"討論現生族群的物質文化與認同感建立之間的關係,希盼能將之所獲得的可能轉變機制的作用過程,運用在關於史前考古的認同研究。 正如前述,同樣的物質文化或稱文本,往往會被不同的人加以閱讀、解釋與詮釋,如在民國初年,對於中華民族構成的討論,往往不同的學者會利用相同的民族誌資料、人類的體質比較、文獻記載、考古出土器物與其他物質文化遺留,分別建構出不同的族群邊緣。筆者在"中國邊緣再造"研究計畫中,試圖藉由比較民國初年不同學者,對於中華民族構成的討論,並且分析當時的學術背景與時代環境,以求了解中國的族群邊緣是如何在相同或類似的物質文化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中華民族邊緣"。 |
| 我個人的研究興趣是中國上古史,核心關懷在於中國古代政治權力與區域文化之間互動的關係。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從中原中心的角度解釋文化傳播的過程,自從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強調所謂「多元一體」的想法,其實這些解釋中國文明形成的方式很大的問題在於忽視了「中國」形成的概念和過程的演進。從形成的過程這個角度和視野中,是我思考中國上古史的方式。 落實於實際的研究當中,我的碩士論文計劃從古代成都平原的文明如何進入華夏的過程著手,初期的思考是從文獻和考古兩方面瞭解成都平原在古代文明中的特殊性和高度的發展,三星堆的發掘基本上是證實了這樣的思考。而燦爛的古蜀文明為何在西漢前期即被遺忘,這是我未來碩士論文的基本方向。 長期的方向大致打算從古代的成都平原出發,在時間和空間上加以延伸,其一,與中原國家、長江下游的城址、器物和文明的形成做比較;其二,往南與雲南、越南和東南亞的古代文明進行比較,拓展研究的基盤。 |
| 加入這個團隊不過是最近的事情,對於一個歷史系的學生而言,少數民族是一個值得關心卻又缺乏接觸的領域。我從台灣史的關懷,漸漸觸及中國西南的邊陲民族,同樣的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珠,感覺是那麼熟悉又陌生。雖是同種族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雖然總有差異,然骨子裡的血統與文化,卻又相似到跟村里鄰居差不多。林林總總的模糊印象,都是欠缺瞭解的代表,只要有接觸,天似的鴻溝說跨過也就跨過了。 由於第一次接觸數位典藏的計畫,對於資料庫的規劃流程與規劃得花不少心力,這當然也涉及很多部門的配合與協助,如資科所、民族所、傅斯年圖書館等單位的鼎力支持。這個計畫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起點,也許呈現出來的不會盡善盡美,但這背後包含許多人的努力與付出,卻是值得肯定與掌聲的。 |
| 曾自詡為史學工作者,現今成了人類學的門外漢,加入這個工作團隊只能算是一個偶然。 對於「數位典藏」的瞭解,僅僅停留在研究所時期耳聞的一個計畫,那時的想法,認為數位典藏不過就是簡單的掃瞄工作而已,與自己在家中用掃描器掃瞄照片沒有什麼兩樣。直到加入計畫之後才知道,數位典藏原來不只是「數位」與「典藏」而已。 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計畫裡的豐富著實讓我大開眼界。從檔案實體的數位化開始,到資料庫完成建置公諸於世,中間牽涉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原來是如此地繁複與深奧。然而,這僅僅只是計畫的執行層面而已,計畫的意義與價值其實才是重點。儘管,我們所做的也許還談不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的偉大事業,但這確實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使命。 中國西南地區,一個被歷代政府視為「蠻夷」的地方,隨著民初的「中國邊緣再造」運動而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無論是人類學或是歷史學者,這樣一個問題都令他們充滿興趣。儘管,許多朋友都問我:「這個有什麼好研究的?」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爬過那堵「先入為主」的高牆,自然不能一窺廟堂之美、殿堂之深,當然,也就不能體會到這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園地。 在龐雜且多元的西南少數民族研究中,最令我醉心的,應當是他們豐富而多彩的神話故事。從洪水神話、兄妹神話,到三兄弟的故事與盤瓠王的傳說,這些我們在小時候聽過的故事,原來,他們都來自於中國西南地區。這些故事的背後,其實都是早期人民心中對於「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的疑惑與想望。就像天空中充滿故事的星星一樣,西南的一草一木,也都有他們的傳說與想像,就這樣,我一股腦兒地掉進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漩渦裡。 |
|
我的碩士論文探討的是台灣布農族的狩獵文化,因為長期登山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接觸到狩獵文化與生態議題之間的拉扯,讓我想瞭解在所謂現代化的今天,狩獵的實踐所展現的意義。畢業後,也一心想做台灣的研究。 不經意進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工作領域,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以往總是將眼光侷限於台灣,認為只有台灣的議題才是有趣的。因為數位典藏的工作,讓我有機會到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地區走訪,發現這個中國西南偏遠的地區,文化是如此豐富多樣,而生活於其中的族群,更是與整個東南亞的族群息息相關。我領略到,人類學家研究的主題是人與其文化,而不應將眼光侷限於某一特定地區,否則將失去看見更多文化可能性的機會。 |
| 生逢世界偉人暨民族救星逝世,目睹二十年來黨國神話崩解以及追求民主的陣痛過程。試圖在理想幻滅與神聖除魅的後現代沙灘上,撿拾意義裂解後的碎片。 生性念舊,雖曾為歷史學之逃兵,轉投民族學之懷抱,但對前者仍不能忘情。試圖同時討好舊愛與新歡的結果,是寫出一篇從歷史人類學切入清朝滿洲文化復興運動的雜燴論文。 從小喜歡簡單與熟悉的事物,但長大踏上文化與歷史研究之路之後,才發現自以為簡單的其實並不簡單,而自認為熟悉的也不再熟悉。一路走來,心中滿是惶恐與驚喜。如今踏入中國西南研究的新領域,翻閱著前輩的發黃手稿,不禁讓我遙想那個艱困卻風雅的年代,前輩學者的斯文風範讓人欽慕。不清楚未來能夠留下些什麼,至少在這個村寨網留下自己走過的跫音。 |
|
我的研究重心放在漢代社會,尤其是東漢末年大一統王朝崩解的過程。碩士論文以東漢流民為主角,卻旁枝末節討論了許多相關問題,其中包括了西北地區羌漢雜居對東漢王朝的影響。若非從史書抽絲剝繭,身處歷史洪流的東漢諸帝王將相們恐怕很難相信,時代巨變居然肇因於他們對西北「蕞爾小患」的生活習性認識不深。 中文系的學生大多專注於古典詩詞、中國思想或文字的研究,我則一向喜歡從宏觀的角度去看歷史。因緣際會加入了這個計畫,又擴展了一些民族人類學的視野,打破了許多族群「邊界」的成見。儘管如此,這一年來(2008)還是常常捫心自問:我希望擁有的學問從哪裡來?想要跨界到哪裡去?我的肩膀能扛起多少責任?能否為臺灣小小的學術圈盡一些棉薄之力? 幾乎沒走過田野的我,未來,真的還有很多很多需要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