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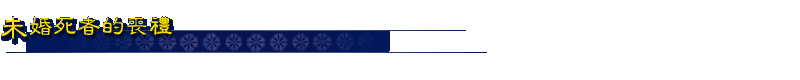 |
|
|
|
| |
|
一個人是否能享有一場理想喪禮,取決其是否具有已婚的社會身份。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哈尼人又該如何面對一個未履行婚配義務即死去的人?
一 、未婚女性的喪禮
對於年屆已婚條件但卻未婚而亡的女性, 哈尼人並不在家屋舉行喪禮,只在死者埋葬後, 喪家準備大量的糯米粑粑,邀集同村男性(包括父系親屬與非父系親屬),
到她的墳前燒吃糯米粑粑。 此外,喪家還要在墳前燒掉一些 器具用品, 如裝衣服用的竹簍、織布機、織布繞線的器具,以及象徵田中小屋的茅草搭就的屋子等。這些被焚燒的器物,都是喪家為了在死者墳前焚燒所新製的,比擬作活人所使用的一般家俱、器物。
 |
|
 |
| 裁布作衣的哈尼婦女 |
|
裁布作衣的哈尼婦女 |
一位男性村人在向我描述完一場三年前死亡少女的喪葬儀式之後,告訴我說,這些被拿到墳前焚燒的與做布有關的物品,意思是把家中的家俱、物品燒給死掉的女孩子使用、居住。當時已經在哈尼村中居住好一段日子的我,已經清楚知道哈尼社會中的「布」的一整套製作過程,都是屬於「女人的事」,哈尼女人必須負責生產「布」,而這些在墳前焚燒的物品實則是代表「女人的物」,象徵性地指涉「女性」。儘管已有這些了解,我還是習慣性地在聽完村人對於某些現象、儀式過程與內容的描述後,詢問為什麼。
我問那名男性村人為什麼燒掉的都是與做布有關的器物時,他一副理所當然地表示:「因為那是女人會用到的東西」。我又問他:「為什麼是把東西燒掉呢?」「燒給她用啊
?」村人答道。「可是一般的喪禮(指已婚死者的喪禮)不是就把那個代表房子的zo mu 
| 在已婚死者的喪禮中,放在死者棺木上的三角錐木架,具有「家屋」的象徵意義。 |
放在墳前,擺著讓它自己爛嗎 ?」我問。村人略有遲疑地答道:「……沒有結婚的不一樣。」我又問:「為什麼死掉的女孩子是燒給她用茅草搭的田中小屋
?」男性村人想了想,突然心領神會地笑了笑,說道:「沒有結婚的女孩子不能待在家裡面,只好給她住在村子外面的小屋子。」
比較已婚死者的喪禮,可以發現在儀式過程中並沒有焚燒物品供死者使用的象徵行為,在已婚死者的喪禮中,在概念上,能帶到祖先聚集之地的物品,如牛、豬、拐杖、雨傘、家屋等,是藉由生者獻祭與放置器物在墳前任其自然腐朽的方式,來象徵性地轉化給死者擁有;而在未婚女性的喪禮當中,哈尼人卻以火焚的方式來處理象徵燒給死者使用的「女人的物」。對應著並不強調死者性別差異的已婚死者喪禮,未婚女性喪禮中的儀式象徵物重點在於強調死者的性別屬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喪家的男性親屬與同村男性非親屬在墳前焚燒標幟著具有性別屬性的「女人的物」,實是男性集體象徵性銷毀處於非正常狀態下的未婚女性死者。我們可以從喪禮焚燒物的其中之一的茅草搭就的田中小屋,看到哈尼人對於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哈尼女性,但卻未婚而亡的“非常態”界定。
哈尼人聚集而居,而且他們很強調村寨邊界的概念,每年都會舉行用寨繩劃分寨內與寨外、將鬼怪趕出寨子等確定寨界的儀式。對於聚居的哈尼人而言,田中小屋絕非一般概念下正常、合適的居住家屋,
| 一般而言,田中小屋是村外、供耕種或放牛的人避雨、休息的地方。鮮少作為人的正式居所,有時或有瘋人會以小屋為棲身之處,但也不能算是正常的家屋。 |
其位置處於村寨邊緣,相對於居住於村寨內的「家屋」,更顯示出它的反常性。
在已婚死者喪禮中,放在死者棺材之上的錐形木塔dzo mo 象徵著死者的「家屋」,在喪葬結束後,這個「家屋」象徵物被繼承死者的兒子手拿著dzo
mo,並放置於死者墳墓前,任其自然腐朽。相對於象徵「家屋」的錐形木塔,在未婚女性喪禮中焚燒的茅草搭就的田中小屋,便顯出對立的象徵意義。
在婚後隨夫居的居處制度下,女性在結婚之後搬到丈夫家中居住,死後,也依循巫師背誦的指路經與夫方祖先的名字,魂歸丈夫的父系祖先聚居處。在此種情形下,未婚即死的女性沒有歸處,所以在喪禮中,藉由焚燒田中小屋,象徵性提供給未婚女性死者居住。這是父系繼嗣制度與婚後隨夫居制下不得已的安排,但也藉由此種儀式展演,哈尼人解決了未能嵌入文化系統安置內的未婚女性的問
題,讓他們住進位處於邊緣、村寨之外的田中小屋。
然而,與其說,在墳前焚燒這些器物是為了給死去的女性在死後的世界使用,不如說,未婚女性喪禮中的儀式行為是在標示死者本身的女性屬性、也標示出因為她未婚而死所造成的邊緣、反常態性質。在墳前焚燒織布機、繞線器等女人的物的儀式行為下,死者的女性屬性再次被強調,經由焚燒的儀式行為,也同時象徵性地銷毀未被納入聯姻體系下的女性性徵。
面對女性本身擁有但卻未能發揮的聯姻條件,在未婚女性的喪禮中,哈尼人也以同村男性燒吃糯米粑粑的儀式行為,來消化與吸收未婚女性死者的潛在聯姻能力。在哈尼人的婚姻過程中,給妻者送到討妻者的糯米粑粑是伴隨著女人的流動而產生,屆適婚年齡的女性本身具有使其父系家庭多一個聯姻群體的潛力,卻因為死亡而使得聯姻成為不能。在未婚女性的喪禮中,喪家準備大量糯米粑粑供同村男性食用,這種現象違背了一般狀態下對糯米粑粑的使用概念。
Levi-Strauss(1969[1949])指出,母方交表婚的婚配形制使得各個不同的父系群體普遍地交換女性,女性作為聯姻交換物,聯結了兩個父系社群,使得社會關係的拓展成為可能。在強調普遍交換的哈尼社會裡,每個父系群體中的女性親屬成員被預期會婚出到另外一個父系群體中,並帶走原生群體的糯米粑粑,供養她的婚入群體,而仰賴著給妻群體的糯米粑粑(作為食物的源頭)的供養,使得父系群體得以繁衍。女性的流動實代表社會中全面性的食物(糯米粑粑)得以流動循環,而人與社會的再生產也得以持續進行。
一名未婚亡故的女性,代表預期的婚姻落空,即表示食物(糯米粑粑)流動的停滯,一個父系群體的糯米粑粑本應隨著女性親屬成員嫁出而轉移到另一個父系群體,但因為女性未婚而死,社會全面性交換糯米粑粑的流動因此中輟,這實則代表社會與人的再生產的停滯。在未婚女性喪禮中,同村男性燒吃糯米粑粑的行為,實則是在父系制度、不平衡交換婚制下,由同村男性消費女性的聯姻能力,以及消費象徵食物營養來源的糯米粑粑。透過喪禮中同村男性集體食用糯米粑粑,解決了原先社會再生產與食物再生產停滯的困境,經由共食糯米粑粑的儀式,象徵性地將女性結婚、生育能力與營養回歸父系群體自身,將潛在聯姻能力與因為聯姻而能流通的食物營養反向供給本來就與該父系家庭建立起社會關係的地方社群。
二、未婚男性的喪禮
未婚男性的喪禮是另一種表面形制上完全不同的儀式舉行方式。在適婚年齡死亡的未婚男性,喪家會在自己家中殺一頭公豬,獻祭死者,並請巫師「畢摩」為死者背「指路經」,
| 相較於已婚死者喪禮中的「指路經」,為未婚死者所念誦的「指路經」簡略得多,主要是少了唸誦聯姻群體來獻祭的部份,此外,不同於已婚死者喪禮中有多位巫師「畢摩」的參與,在未婚死者的喪禮中只有一個「畢摩」來背喪禮。 |
引領死者找到祖先聚居之地,但由於死者未婚而死的身份,畢摩在喪禮中不能背誦家譜,使得死者的名字不能嵌入父系家譜所記錄的祖先名字當中。在埋葬死者過後,喪家邀請關係較親近的親屬與村人到家食用作為犧牲的公豬,以此結束喪葬儀式。
比較為已婚死者舉行的喪禮,在埋葬死者身體過後的隔日,喪家與其父系親屬共同食用聯姻群體帶給喪家的喪豬肉。食用喪豬的目的,在於「豬」所表徵的性徵與繁衍能力,藉由食用象徵生殖繁衍的營養食物,在概念上,增強死者父系群體的生育力,幫助再生產新的親屬成員,以此,父系群體得以修復成員死亡的損失,人的再生產得以延續。
在已婚死者的喪禮中,食用喪豬,具有一個父系群體象徵性地再生產新的親屬成員的儀式意義,而在未婚男性死者的喪禮中,面對可以傳承世系的男性親屬成員亡故,喪家與親屬食用自己所準備的喪豬,除了強調再生產新成員的意圖之外,喪豬也象徵性地替代死者,在喪禮中,經由被食用的喪豬,父系親屬象徵性地消費死者,回收死者。
因此,面對未婚女性死者的喪禮中,為何未有食用喪豬的儀式行為?我們必須將之放置於父系制度來理解。在父系制度下,女性終有一日必須婚出,經由婚姻,女性成為夫家成員,在她的喪禮中,她的名字是嵌入在夫方的祖先名字當中,死後成為夫家的祖先,總之,女性身份的歸屬必須經由婚姻定義到丈夫的父系群體當中。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個父系群體而言,它的未婚女性成員雖然死亡,但它失去的是一個能夠為它創造聯姻關係的連結成員,而並不是一個傳承世系的成員。在父系制度下,哈尼女性最終的歸屬並不是父系群體,而是她丈夫的父系群體。對於一個父系群體而言,它並不能夠「消費」
自己群體中的女性成員(但它會消費該女性的聯姻能力),也因此,在未婚女性的喪禮中也就不像未婚男性的喪禮一樣有殺豬的必要。
分析未婚死者的喪禮,我們看到的是,未婚而亡的死者因為無法完成社會的再生產與人的再生產的循環模式,這種缺憾反應在喪禮中,便形成未婚喪禮的儀式內容的重點在於解決婚姻循環停滯的困境。反映在未婚女性的喪禮中,面對社會再生產的停滯,男性藉由共同食用聯姻象徵物---糯米粑粑,一起消費、吸收未婚女性死者的原有潛在的婚姻能力。而婚姻循環停滯的困境反映在未婚男性的喪禮中,則有死者的父系成員食用替代死者的公豬肉,以此象徵行為,消費且回收死者。 |
| |
| |
 |
在已婚死者的喪禮中,放在死者棺木上的三角錐木架,具有「家屋」的象徵意義。 |
 |
一般而言,田中小屋是村外、供耕種或放牛的人避雨、休息的地方。鮮少作為人的正式居所,有時或有瘋人會以小屋為棲身之處,但也不能算是正常的家屋。 |
 |
相較於已婚死者喪禮中的「指路經」,為未婚死者所念誦的「指路經」簡略得多,主要是少了唸誦聯姻群體來獻祭的部份,此外,不同於已婚死者喪禮中有多位巫師「畢摩」的參與,在未婚死者的喪禮中只有一個「畢摩」來背喪禮。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