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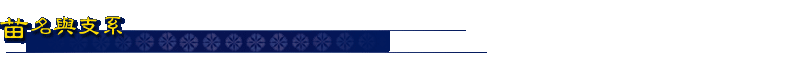 |
|
|
|
| |
|
| |
苗族的居住地北至鄂南湘西南至越北、老窩、泰北,綿延兩千公里,在中國境內的苗族,主要與漢人雜居,不同地區的苗人還分別與侗族、布依族、壯族、彝族、土家族、黎族雜居,在越北老窩泰北主要與Karen等高地族群雜居。歷代以來,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多以苗夷稱之,文人騷客對西南地區各式各樣的少數族群,也無從分辨,到底哪些族群是「苗」、哪些不是「苗」,經常是自由心證,各家用法莫是一衷。這種情況,著時困擾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來自西方、日本的民族學家或人種學家,甚至是中國的民族學家。《邊事研究》第五卷第五期有一篇名為〈滇邊苗族雜談〉的文章,謂:「雲南苗人,多數居在西北連山一帶,而尤以永兆、嚴江、蘭坪、維西各縣為最多……苗人的種類,本有紅苗、花苗、黑苗、短鼻苗……之分,惟當地漢人則均稱之約
"栗粟"。(笑岳: 85,民國年間苗族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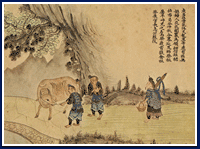 以今觀古,或許會覺得很可笑,笑岳或許不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學家,但《邊事研究》的編輯群可是由數位當時知名的民族學家、邊政專家組成,不應該不知「苗」與「栗粟」實為完全不同的族群。然而,當「苗」這個字用來指涉族群名稱時,有些時候指的是所有的非漢民族,有些時候又指稱居住在貴州的少數民族,有些時候又是指說苗語、他稱青苗、白苗等的非漢族群,《苗蠻圖冊》、《百苗圖》、《黔苗紀略》等被認為是研究明清時期苗民生活情況與地理分佈最好的文本,卻也不難發現,雖名為「苗」書,狪人、犵狫、猓玀皆在其中,又明清以降西南地區的地方誌大量出現各式各樣的苗名,據統計有160種之多。 以今觀古,或許會覺得很可笑,笑岳或許不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學家,但《邊事研究》的編輯群可是由數位當時知名的民族學家、邊政專家組成,不應該不知「苗」與「栗粟」實為完全不同的族群。然而,當「苗」這個字用來指涉族群名稱時,有些時候指的是所有的非漢民族,有些時候又指稱居住在貴州的少數民族,有些時候又是指說苗語、他稱青苗、白苗等的非漢族群,《苗蠻圖冊》、《百苗圖》、《黔苗紀略》等被認為是研究明清時期苗民生活情況與地理分佈最好的文本,卻也不難發現,雖名為「苗」書,狪人、犵狫、猓玀皆在其中,又明清以降西南地區的地方誌大量出現各式各樣的苗名,據統計有160種之多。
一百六十多種的苗名,或以服飾、或以習俗、或以地區、或以職業等命名,並無統一的命名原則,居住在同一地點同一地區的一群人,也可能會有兩種以上的名稱,比如鴉雀苗,又稱牛屎苗,概不同人不同時間所做的描述,又沒有詳細考證索引即任意命名,所造成的混亂情況。然而,這種人群名稱混亂的情況,卻值得我們思考更根本的問題:傳統的「族名」觀是否即是西方的「種族」觀,或是今日的「族群」觀呢?明清地方誌所提到的各式各樣以苗為名的人群,是否暗喻其為有共同血緣的同一「種族」,或是有共同風俗、語言、血緣與心理素質的同一「族群」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傳統的「族名」,並不等同於「種族」或是「族群」的概念,其中細微的討論與嚴謹的論證非本文所能處理,在此僅以《皇清職貢圖》的成書過程為例,說明清乾隆年間,史冊、地方志中非漢族群,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被命名、被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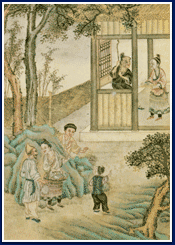 《皇清職貢圖》序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初一上諭說:「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著沿邊各督撫,於所屬苗、瑤、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匯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在乾隆皇帝的倡導下,各民族地區的官吏都爭先請畫師繪製,出現不少民族地區風俗畫,如《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等,並彙集中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欽定宮廷畫師丁觀鵬、金廷彪、姚文瀚、程梁分別繪製《皇清職貢圖》。經過四年的繪製,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終告完成。事後各地官員也將本地民族圖冊,臨摹轉抄,送給友人,因此流傳於民間(李宏復,南京博物院)。《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苗蠻圖冊》、《番苗畫冊》等這一類圖文並茂的畫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今日中西學者將其統稱為「苗蠻圖冊(Miao
Albums)」。 《皇清職貢圖》序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初一上諭說:「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著沿邊各督撫,於所屬苗、瑤、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匯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在乾隆皇帝的倡導下,各民族地區的官吏都爭先請畫師繪製,出現不少民族地區風俗畫,如《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等,並彙集中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欽定宮廷畫師丁觀鵬、金廷彪、姚文瀚、程梁分別繪製《皇清職貢圖》。經過四年的繪製,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終告完成。事後各地官員也將本地民族圖冊,臨摹轉抄,送給友人,因此流傳於民間(李宏復,南京博物院)。《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苗蠻圖冊》、《番苗畫冊》等這一類圖文並茂的畫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今日中西學者將其統稱為「苗蠻圖冊(Miao
Albums)」。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的畫冊圖集,是「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於所屬苗、瑤、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且謂「不必特派專員」。顯然,這一類的畫冊,雖是以「民」為主體,卻不脫「地方誌」的原則,乃是紀錄「一地之民」或「一府之民」。以《百苗圖》為例,對每一族名所指涉的人群,必先說明居住地,然後才列舉其服飾、風俗的特點,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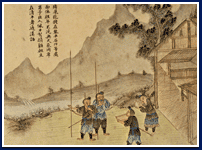
| |
打牙仡佬-「打牙仡佬在大定府平越州清鎮縣。女子出嫁先折去門牙二齒,謂恐害夫家。」同一族名所指涉的人群,其分佈區域大小不一,但總是方圓鄰近地區,不會有東一群人與西一群人共有同一族名的情況。這說明「族名觀」指的是在某一地區的某一種人群,而非西方「種族觀」以血緣為基礎結合不同地區的人群,或是「族群觀」以文化凝聚各種人群。在「族名觀」的邏輯下,同一群人到了不同地區,就變成了有另一族稱的另一群人。 |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間,曾於西南地區做過數次大規模的民族調查,其中苗族社會調查一直是其中的重點。影響較大者,有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書、芮逸夫胡慶鈞等人的川南苗族調查、大夏大學的陳國鈞吳澤霖主持貴州各地苗夷社會調查、楊漢先寫的一系列介紹大花苗的文章、岑家梧在嶺南大學期間主持苗族社會調查、王興瑞的海南苗族調查、楊成志在中山大學帶領一群學生於兩廣地區進行苗夷社會調查等等。概括而言,調查區域遍及苗族的分佈區域。這些早期的民族學家的確被地方誌古籍裡五花八門的苗族名稱困住了,有如楊漢先、芮逸夫等積極的將紛雜的苗名簡化成幾大類別,如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等,至今尚有不少學者沿用﹔也有主張將「一概廢除,重新識苗為一類」者。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間,曾於西南地區做過數次大規模的民族調查,其中苗族社會調查一直是其中的重點。影響較大者,有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書、芮逸夫胡慶鈞等人的川南苗族調查、大夏大學的陳國鈞吳澤霖主持貴州各地苗夷社會調查、楊漢先寫的一系列介紹大花苗的文章、岑家梧在嶺南大學期間主持苗族社會調查、王興瑞的海南苗族調查、楊成志在中山大學帶領一群學生於兩廣地區進行苗夷社會調查等等。概括而言,調查區域遍及苗族的分佈區域。這些早期的民族學家的確被地方誌古籍裡五花八門的苗族名稱困住了,有如楊漢先、芮逸夫等積極的將紛雜的苗名簡化成幾大類別,如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等,至今尚有不少學者沿用﹔也有主張將「一概廢除,重新識苗為一類」者。
二十年代末期語言學、體質人類學與民族學在中國的發展,被視為是用科學方法解決非漢族群人種問題的唯一方式,很快的語言學的快速發展,解決了所有民族與支系的爭議,取代了其他學科,建立了一套分類廣大的非漢民族的科學標準。以苗族的例子而言,若說「語言創造了一個民族」,是一點也不為過。今日百多種的苗名,已逐漸被淡忘,連當地的苗人也不知曾有這樣的稱呼,研究者研究某一地區的苗人社會,也不再考究當地苗名的遞變,今日大多數人比較關心的,反而某地的苗人是屬於哪一支系的苗族,然後預期當地苗人與其他地區屬同一支系的苗人在語言、文化、風俗、歷史上大同小異。
當代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中外學者,區分苗族支系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地方誌、古籍的記載中依據服飾顏色,分成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五大支系﹔其二是依其語言不同,區分成三大或五大方言,各方言下再細分成數種次方言或土語。前文我們已經介紹了語言的分類方式,接下來介紹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五大支系苗族的分佈。
| |
苗人,槃瓠之種也……盡夜郎境多有之。有。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峒溪籤志,引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79) |
 清康熙年間陸次雲《峒溪籤志》即謂苗人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五種,清初以後,其他文獻如《黔中雜記》等,也多依其服飾區分,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作為苗族的主要支系。這種區分,「當然不夠科學,但大致還是反映了苗族內部不同支系的存在這一客觀事實,並且約定俗成,有些稱呼已習以為常,至今仍為苗族自己所沿襲使用」(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0)。伍氏根據1987年雲南田野調查的親身體驗,認為苗人使用白苗、花苗等稱呼十分自然,因此認為「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一些稱呼(只要不帶誣蔑和歧視性質的)來表述苗族內部存在的不同支系是可以的」(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0)。不過,各種不同的苗名,也有不包括在此五大支系之內的,如洞苗、箐苗、陽洞羅漢苗等,再加上滇南文山各地、黔西北與滇東北各地實地考察蒐集到各種自稱與他稱,如花苗又分大花苗、小花苗,青苗、白苗外還有漢苗及其他分支,伍氏最後的結論竟是推翻前文主張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五大支系說,反而宣稱:「苗族的大小支系繁多,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五支只是舉其大者」(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4)。 清康熙年間陸次雲《峒溪籤志》即謂苗人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五種,清初以後,其他文獻如《黔中雜記》等,也多依其服飾區分,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作為苗族的主要支系。這種區分,「當然不夠科學,但大致還是反映了苗族內部不同支系的存在這一客觀事實,並且約定俗成,有些稱呼已習以為常,至今仍為苗族自己所沿襲使用」(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0)。伍氏根據1987年雲南田野調查的親身體驗,認為苗人使用白苗、花苗等稱呼十分自然,因此認為「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一些稱呼(只要不帶誣蔑和歧視性質的)來表述苗族內部存在的不同支系是可以的」(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0)。不過,各種不同的苗名,也有不包括在此五大支系之內的,如洞苗、箐苗、陽洞羅漢苗等,再加上滇南文山各地、黔西北與滇東北各地實地考察蒐集到各種自稱與他稱,如花苗又分大花苗、小花苗,青苗、白苗外還有漢苗及其他分支,伍氏最後的結論竟是推翻前文主張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五大支系說,反而宣稱:「苗族的大小支系繁多,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五支只是舉其大者」(伍新福、龍伯亞
1992: 184)。
伍新福從歷史學的觀點,討論苗族支系的形成過程,言下之意,似謂苗族的支系種類繁多,五大支系是歷史過程中所形成較穩定的支系,其他大小支系仍在形成中。其結論卻是保守且模凌兩可,一方面合理化不需要討論小支系形成的理由,另一方面卻又不排除五大支系外尚存在其他多種小支系。我以為這不是個高明的做法,充其量只是個方便選用史料的做法,畢竟明清以來的史料中最多的是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為名的材料,繼田雯《黔書》,李宗昉《黔記》之後,大量出現的苗名,除可包含在五大支系之外的其他苗名,就不再伍新福討論支系形成的範圍內,令我疑惑的是,伍新福又是如何分辨哪些是包含在五大支系內,哪些又是不包含在五大支系內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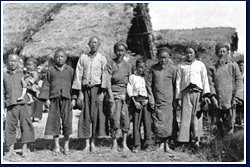
伍氏對苗族支系的區分的模凌兩可,同樣發生在所有試圖區分苗族支系的研究中,五大支系的說法,充其量只是「反映了苗族內部不同支系的存在這一客觀事實」,雖然是「約定俗成」的區分方式,近代研究苗族的學者也有不少採用,但是否皆指涉相同的人群、分布地點,可就不一定。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