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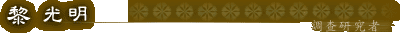 |
| 附記王元輝先生 |
| |
我們要如何介紹黎光明先生這個人?他在學術上並無偉大成就﹐事業屢經波折巔沛﹐人格上或有瑕疵﹐最後死於一個有太多可歌可泣故事而使其事功難以彰顯的亂世之中。
黎光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早期的研究人員之一。他留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這一部「川康民俗調查報告」﹐寫成於民國十八年﹐他的民俗調查之旅則是始於民國十七年──也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草創之年。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安陽殷墟發掘」﹐以及傅斯年、李濟等學者﹐廣為社會所知﹔然而黎光明先生﹐即使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當然﹐對於一個中國當代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來說﹐「學術成就」是其成員是否能留名的重要因素﹔黎先生在本所並未久任﹐也沒有顯赫的學術成就﹐自然很少人知道他了。他的這一本「川康民俗調查報告」手稿﹐在史語所的圖書館裡塵封了七十四年﹐多少也反映其被認為學術價值不高的緣故。
關於黎的生平﹐可參考的文獻不多﹔以下我主要賴三種文獻﹐來介紹這個人﹐以及本書另一作者王元輝。這三種文獻﹐一是《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志》(簡稱阿壩州志)之「人物志」中有關黎的介紹﹐一是王元輝所著《神禹鄉邦》中一篇「黎光明先生傳略」﹐最後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公文檔案中有關黎的一些記載。
| 州志資料見於﹐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志》(成都市
: 民族出版社﹐1994)﹐頁 2604-2605。有關傅斯年與黎光明之來往電文﹐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公文檔﹐原檔號﹕元
115-20-1﹐元 115-9﹐元 230-9, 230-10, 230-11,。王元輝之著作﹐見王天元﹐《近西遊副記》(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神禹鄉邦》(台北﹕川康渝文物館﹐1983)。 |
三種資料出於三種不同的文類(genre)──方志、回憶錄、公文書。三種文類﹐作為三種結構性社會記憶媒體﹐各有其特殊意義。
黎光明較詳細的生平事蹟﹐見於《阿壩州志》之中。根據此文獻﹐黎光明字勁修﹐回族﹐灌縣灌口鎮人。他生於1901年﹐死於
1946年。民國十一年﹐他曾在南京東南大學史學系就讀。後來因加入國民黨﹐參加學生運動﹐「反對反動軍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被東南大學開除。旋至廣州﹐進入中山大學就讀﹐民國十六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王元輝的回憶錄《神禹鄉邦》中﹐相關記載與此類似﹔稱其「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加入革命行列﹐從事反軍閥的學生運動」。
《阿壩州志》中又記載了一段插曲。黎至廣州﹐原來是要進入黃埔軍校。但因其信奉回教﹐「恐軍旅生活難符教規﹐而改讀中山大學」。在王元輝對黎光明的回憶中﹐稱「他原來的老朋友們都已紛紛棄文習武﹐進入黃埔軍校﹐他因信奉回教﹐恐軍隊生活對他不方便﹐所以留在中大畢業。」這不僅說明了黎個人的一重要生涯抉擇背景﹐也說明在那時代黎之交往社會圈──王元輝也是此圈中人之一。參與五四學生運動﹐後又因故未進黃埔軍校﹐對於黎光明一生事業顯然有極大的影響--後來他一直輾轉流離於革命救國與教育文化兩種志趣之中。
黎光明畢業於中山大學後﹐在民國十七年﹐任職於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自然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籌備處當時設於廣州中山大學有關。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該年七月完成立所﹐黎光明於八月底由上海啟行﹐據傅斯年之年度報告稱﹐「助理員黎光明……託其往川邊作民物學調查」。由此可見黎可謂是此所之創始研究人員之一。他九月底至成都﹐遷延至民國十八年一月始邀集朋友﹐一同西向往岷江上游去。此時又發了幾個電報﹐請傅斯年寄差旅費來。傅對他滯留成都﹐以及呼朋引伴前往相當不悅。在民國十八年二月十六日致黎君的信中﹐傅一再訓斥叮嚀﹐「千萬不要在成都一帶交際」﹐「細心觀察﹐少群居侈談政治大事」﹐並對其此行花費太大﹐「只索錢不報告」﹐頗有微詞。與黎共同前往的﹐第一次可能有數人﹔在茂縣北的疊溪受阻於戰事後﹐他們返回成都。當年三月黎光明又前往松潘地區﹐此時只有王元輝陪同。他們在同年六月結束此考察行程﹐返回成都。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已遷往北平﹐黎回北平報到﹔少不得﹐又受到傅斯年許多申斥。
黎光明先生離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間﹐應就在民國十八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公文書中﹐有一件為傅斯年上文院方要求處罰黎光明的文件。原因是黎私自在圖書閱覽室中會客﹐「大防害他人工作不言可喻荒謬如此」﹔又稱「黎君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傅因而請院方予以記大過一次。
《阿壩州志》對黎光明之事業生涯述之甚詳。離開史語所後﹐民國十八年﹐他至燕京圖書館工作。民國二十至二十一年﹐任教於成都大學與四川大學。民國二十二年﹐他至江西星子任中央軍校特訓班教官。民國二十三年返川﹐又先後任教於重慶大學、四川大學。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他回到軍政職務上﹐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上校政治教官。民國二十七至三十年﹐黎先後在綿陽中學、成都蔭唐中學任校長之職。民國三十年﹐他在政治上相當活躍﹐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部幹事兼書記、國民黨成都市黨部委員、成都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民國三十一年﹐又從事教育﹐任省立成都中學校長。民國三十二年﹐任十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秘書。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他就任靖化縣(今金川縣)縣長﹔同年三月﹐即遇害死於縣長任上。
以上經歷﹐可見他一直在政治與教育文化兩種職志間的徘徊。王元輝在其回憶錄《神禹鄉邦》中﹐更表達了當時「朋友們」對黎之所事的看法﹕
| |
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到燕京大學圖書館﹐以後幾年的教書﹐兩度當校長﹐越見使得朋友們認他是純粹的讀書人﹐且有人認為他是書呆子。他那裡心服?所以他離開教育工作﹐去參加青年團團務工作。後來又去茂縣作十六區專署的秘書。 |
黎光明先生得以在《阿壩州志》中留名﹐顯然是因為他作為本地靖化縣之縣長﹐在任上為剷奸除惡而以身殉之故。這段情事略如下述。民國以來﹐鴉片種植普遍深入岷江與金沙江上游地區﹐引來大批黑道秘密社會之頭領、會眾﹐以及許多由川東、陜南地區前來「趕煙廠」之流民。中央政府派川軍前來「掃煙」。但總其事的軍方常以「掃煙」為名﹐與地方豪強毒梟勾結﹐干預、壟斷鴉片市場或逕自掠奪毒品。
| 本地已由鴉片種植獲利的村寨民眾﹐在頭人與外來人的挑動下﹐曾與前來掃煙的川軍作戰──此即發生在民國年的「茂北事件」。 |
為了爭地盤﹐甘軍與川軍亦經常在岷江上游地區混戰。民國二十四年﹐共產黨「長征」部隊流竄至岷江上游地區﹐由此北上進入陜西。國民政府為鞏固此邊區﹐民國二十五年在茂縣建立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及保安司令部﹔此舉亦顯示地方軍勢力減弱﹐而中央政府在本地之軍政力量逐漸增強。民國三十一年﹐四川省府主席張群任命時為保安處副處長的王元輝為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剷煙」。此任命多少與王元輝曾在川康邊區遊歷有關。
王元輝﹐四川灌縣人﹐中央軍校畢業﹐康澤藍衣社成員。他到任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後﹐在川康邊區厲行剷煙行動。民國三十一年﹐他親自率軍至懋功﹐指揮保安團剷煙。結果因過於輕敵﹐受到保護煙苗之民團圍攻。據《阿壩州志》記載﹐王最後困守縣城﹐賴地方勢力出面斡旋﹐才得自懋功脫身。王又支持新任松潘縣長汪一能﹐在松潘地區組織剷煙武力。《阿壩州志》稱汪一能掃煙手段激烈﹐行事不正﹐因而激起民怨﹔在王元輝之回憶文章中﹐他則是一位政聲卓著、銳意改革的好地方官。民國三十二年﹐在一次剷煙行動中﹐汪在會匪與各寨民眾的圍攻下被擒﹐受到凌虐及梟首剖腹之處置。此也是王元輝的一大挫折。汪一能﹐四川南充人﹐早年曾就讀中山大學﹐曾受訓於黃埔軍校特訓班﹐康澤藍衣社成員。他的籍貫、資歷﹐都與王元輝、黎光明有相當重疊。
| 汪一能之事跡﹐見《阿壩州志》﹐人物志「汪一能」﹐頁
2599-2600。 |
民國三十二年﹐黎光明任十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秘書﹔此任命﹐很可能與他的老伙伴王元輝時受命整頓十六區之軍政民事有關。至少可說是﹐在民國十八年的川康遊歷後﹐這一對難兄難弟又一度在此地合作﹐以對抗強大的地方勢力﹔他們的對手是杜鐵樵。
靖化縣沙耳鄉人杜鐵樵﹐是一時代社會產物。在當時川康邊區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各路軍方都需要與地方勢力結合﹐於是產生不少的各種剷煙清鄉司令、幫統、營長﹐與邊防軍參謀、隊長等等地方豪酋。他們同時也是哥老會、袍哥等的會首。杜鐵樵便是如此人物。在民國十年﹐他已是「綏靖團練局長」。1930-40
年代﹐是其勢力之巔峰期﹐先後擔任「綏崇清鄉司令」、「懋軍團聯合辦事處副主任」、「勦匪軍綏崇游擊司令」、「川康邊防總指揮部第二大隊長」等職。杜鐵樵將其總部設在靖化﹐一方面便於操控鴉片生產﹐一方面在此邊區擁兵自重、胡作非為。民國二十九年﹐杜遣其爪牙殺害靖化政府之剷煙人員。民國三十年﹐暗殺靖化縣長米珍未遂﹔又殺鄉長﹐策動袍哥武裝兵員包圍縣城。同年﹐立「西勝公社」統一全縣袍哥武力。民國三十一年﹐槍殺十六區視察員尹健剛。民國三十四年﹐杜侵吞縣府獻糧代金﹐又在地方向百姓勒索及強行攤派金錢。四川省府對其作為始終無可耐何。
| 以上資料見﹐《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志》﹐人物志「黎光明」﹐頁
2604-2605﹔「杜鐵樵」﹐頁 2602-2604。 |
黎到靖化任後﹐杜鐵樵處處阻攔黎之縣政改革與煙禁政策﹐並藉故挑釁。於是﹐據《阿壩州志》記載﹐黎在專員王元輝的支持下﹐決心設計剷除杜鐵樵。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日﹐黎在縣政府設宴﹐邀杜飲春酒。杜未防範﹐簡從赴會﹐被黎之手下槍殺在縣府中。當晚﹐袍哥武裝匪徒三百餘人圍攻縣府﹔三月三日﹐縣府陷匪。據《阿壩州志》記載﹕「他撤至後院半畝園時﹐胸部被杜的兄弟伙李興武開槍擊中﹐杜錫登上前揮大刀砍劈他的頭部﹐當即倒地命絕﹐腦漿四溢。」在王元輝之回憶文章中﹐則稱﹕「敬修親率自衛隊迎戰﹐戰一晝夜﹐敬修不幸中彈陣亡。」此事被稱作「寅江事件」。在其相關回憶文章中﹐王元輝並未提及自己涉入剷除杜鐵樵之事。
《阿壩州志》又記載﹐黎遇害後無人敢為其收屍。後來還是當地回民說情﹐袍哥才許將之掩埋。國民政府對他的褒令上稱「盡忠職務﹐弗避艱危﹐為國捐軀﹐殊堪愍惜﹐應予明令褒揚﹐用資矜式。」王元輝﹐民國三十八年在胡宗南所設「川陜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擔任秘書長﹐隨軍撤至台北。在行前那一夜﹐一0四師師長傅秉勛與其竟夜長談﹔王將其熟知之川康邊境山川、事﹐歷歷訴授於傅。而後﹐傅秉勛率軍入山與諸土司相結打遊擊﹐造成所謂「靖茂暴亂」與「黑水戰役」--此為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最後幾場戰役之一。

| 關於黑水戰役請參考﹐郭林祥﹐《陸上台灣覆滅記--黑水蘆花勦匪紀實》(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王明珂〈陸上台灣﹕黑水的過去與近況〉《歷史月刊》141(1999)﹕4-10。 |
我們要如何評價黎光明與王元輝這兩位先生?一對好友﹐在 1929年結伴作川康民俗考查之行﹔1943-46﹐又共同在此地掃奸除惡﹐而屢遭困頓或竟以身殉。
黎光明先生在過去半個世紀﹐幾乎完全被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後輩同僚所遺忘﹔所記得的﹐只是在公文書中所見「只索錢不報告」、「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在圖書閱覽室中會客……荒謬如此」之黎君。我們無理由懷疑史語所公文書中有關黎光明之記載的真實性﹐但這些被選擇記錄而對黎君有負面描述的「事件」﹐也反映了黎的一些人格特質--爽朗、重朋友、關心政治等等。在另一方面﹐公文書可謂是某種社會現實與權力結構下之產物﹔我們也可以由這些公文書中﹐察覺當年國族主義與學術探求之關係﹐以及相關的﹐中央研究院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的權力生態。
黎光明的事跡﹐只見於川西北最偏遠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的州志之中。這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編的「阿壩州志」﹐在體例上沿襲中國「方志」之書寫傳統而有些變革。如「方志」﹐它記錄了許多易被主流社會記憶﹐如正史﹐所遺忘之邊緣人物與事件﹐藉此描述本地的特質﹐並說明「本地」為中國整體的一部分。以此一意義來說﹐黎光明之事蹟被記錄在本書人物志中﹐可說是編撰者以此人與事來再塑造「中國邊緣」﹔以過去之混亂與暴力﹐來強調如今本地之秩序與和諧。比起黎光明﹐王元輝當時在「十六區」有更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阿壩州志》並未替他立傳。偏好為「死節」者立傳﹐也是中國方志書寫傳統之一﹔但王元輝最後得以身免﹐隨軍撤至台灣。他的憶舊文章及回憶錄﹐多由「四川文獻研究社」出版。此出版機構由寓居台灣之川籍人士支持﹔這也反映﹐主要是在鄉土認同中﹐其回憶才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將黎光明、王元輝、傅斯年等人都視為同一時代產物﹔他們被歷史創造﹐他們也創造歷史。在那個國族建構的時代﹐史語所諸學術前輩﹐如傅斯年、芮逸夫、李濟等﹐皆以其學術論述建構國族。

| 早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可謂是以「科學方法」與「新學術」來打造國族﹕從歷史、語言、考古、體質與民族學等角度﹐研究中華民族中各民族之分類與構造﹐及導致此構造的歷史起源與變遷。傅斯年之
「夷夏東西說」、芮逸夫的「中國民族之構成」(大陸 7.1: 25-33, 1953)﹐以及李濟所著《中國文明的開始》﹐可以說都是「社會科學」與「國族主義」結合下的產物。 |
王元輝等人﹐則直接以行動作為獻身於國族建構之中。而黎光明﹐在其殉難前一直徘徊兩者之間。 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屢受斥責﹐與其爽朗好結友的個性﹐以及其交友圈中多燕趙慷慨之士多少有些關連。或者﹐因其「回教徒」身分而未進黃埔軍校﹐是黎光明先生一生事業多轉折而最後終求仁得仁的重要關鍵﹔然而也因「回教徒」身分﹐其遺骸才得以掩埋。但對黎先生這樣奮志於世的人而言﹐一介軀殼又何足道哉。 |
|
| |
| |
| |
|
|